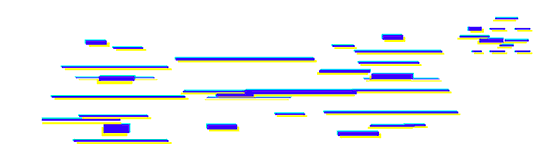查看完整案例


收藏

下载
关
于疫情,我好像没什么可说的,更像是没有参与过,所以我与大多数朋友背道而驰的缩水了三十斤。
我想从大年初二开始说起吧!
在那天之前,我可能还依然在为自己辩解,“我能瘦下来,我在努力做事,我在真诚的创作!”但当你遇到一面镜子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已经臃肿不堪,一切都不像自己说的那样。
大年初二,我把自己关了起来,和世界隔离,我想就算没有疫情我也会这样做,但大环境给我的“工作”造成的障碍也是一个客观原因。
工作室所在这个镇的名字叫青莲,我画的蓝色很多也是用青莲
对面的院子,是李白的衣冠冢
我
主动的被迫回到了几年前在老家租下来的院子,开始了自我反省,我有一种与大家相反的“被世界隔离的感觉”。好像全世界都听不到我的声音(并不是因为疫情),而是一种快要失去自我的真实。体重到了极限,“事业”到了边缘,绘画进入死局。感觉是各种压力把我赶回了老家这个房间。
我面对空空的墙面,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嘛。我好像只能画画。
第一天,脑子里一片空白,又回到了“画什么,怎么画”这个所有绘画工作者都会面对的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。如果说这十年绘画是我逃避现实的庇护所的话,那么现在连这间庇护所的钥匙都搞丢了。
面对着空空的墙壁发呆了很久,不情愿的从库房里拿出了两张十年前留下的两张半成品,又看了很久,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滋味让我不知如何是好,勉强的用一个熟悉的颜色开始往上涂抹,慢慢的有种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,一边画一边意识到,也许这张画不下去的半成品就是十年前意识到问题的开始,满脑子都是这十年的各种问题,写到这里,我想顺着回味一下这十年我的生活,身体,绘画,同步发生的变化和关系。
在
成为独立艺术家之前,我过着工薪族的生活,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自己的小房子画画,时常到天亮,没有任何人看过我的画,也不被任何人关注,艺术在当时就是我一辈子笃定的事,是信仰,与生活无关,与现实无关,关于艺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脑子里思考。
十年前,我的第一批完整的作品有机会在空白空间亮相,我用一种去掉叙事,直指视觉的方式进行表达,画廊同仁的认可和努力推动,加之纯粹的美学形式和运用材料与绘画的关系,让我很快被大家知道并给予肯定。
不
久之后,我失业了,开始适应独立艺术家的生活,有了宽敞的工作室也有了采访和关注,开始与人讨论自己的作品,一次次的对话,把我那些关在小房间里的个人感受曝光在世人面前,从生活到艺术都让我有种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感觉。
原本的朝九晚六变成了昏天黑地,我很想自己对作品的真诚,但一次次的对话与讨论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虚伪,每一次都会从讨论的结果中去修正自己的“观念”(说辞)。我开始怀疑,怀疑大家看到的那种特别,那种少了点苦难的才情。我觉得很轻,正在当时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突变,我要当爸爸了!
给了我一个合理的借口离开北京!
2
012年我回到四川,每天游走在出生的小县城,我想遇见那些记忆中的关键帧,想知道前三十年的自己是如何形成的,我是为什么爱上绘画的,怎么就成了一个画家的,也许知道前三十年怎么来的就知道后三十年该去哪了吧。
离开北京,与人讨论的机会也变少了,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,我很满意。但总觉得缺了些什么,每天看着自己的画也觉得缺点什么,我开始寻找,我所关注的绘画系统,就像想弄明白自己是如何形成的一样。但同时,因为对系统的了解,总想突破,想寻找更多的可能性,与此同时,生活也是,我想重新回到朝九晚六的状态,有一份艺术之外的工作,寻找生活的更多可能性“可能性”这三个字在当时快成我的口头禅了。
工作室附近屋顶的储水罐,我的陶瓷也和它们有关
关
于绘画,此时从纯粹的表达进入到了绘画本身的问题研究,梳理图像与绘画的关系,图像形成的逻辑,我该如何深入的绘画,在题材上和内心表达上回避了情感问题,开始对光以外的物质本身产生兴趣,于是开始了对物质排列组合的分析与研究。
photo by 方正
一方面我组建了一个团队,想在研究材料的同时做出一些产品,从日常的角度输出自己的美感,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艺术以外的知识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积极和阳光,感觉终于回到了半工作半创作的状态,也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可能,但是!这一切都没有我所描述的那么理想。唯一跟我最初想寻找深刻的体验所接近的就是“苦难”。
我
时常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底缺什么,有人出现的时候又会准备好台词证明自己做过了很多工作。这样的循环,直到我遇到那个年轻的自己。那个不知道自己该干嘛,只知道自己不想干嘛的自己,不在乎自己是否成为别人眼中有用的人,宁愿站在原地像个木桩的人。当我看见夕阳洒在金色的海面上的景象时,我的心被触动到了,就差这一点,只要抓住这一点闪过的灵感,这就是我啊。那一刻开始我跟自己说“人生哪有那么多可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,寻找是一种迷失,而等待是最好的寻找
。
”还是用那句用了二十年的签名与自己和解:“站在原点,像个木桩”。
慢
慢感觉自己从尖锐刻薄变得温暖起来,每天专注的在画面里表达,而不是在理论里作画;不再以解压为目的暴食,大概第十天,我摸着塌下去的肚子,突然很享受这种饥饿感,脑子变得更加清晰。以前半夜忍不了的那种饿实际上是馋!是欲望!
到现在这个疫期我想我与自己有好的和解了,瘦下来31斤,回到了刚去北京的体重,感谢那个20多岁的自己,他差点离开我,接下来依然不渴望成功,不希望证明,只希望好好珍惜。
photo by 黎晨驰
客服
消息
收藏
下载
最近